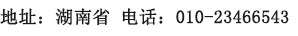视频1:赵县梅花调《骨肉情深》选段,梁素霞演唱
牙板叮当唱梅花,渔鼓声声说道情
文/图燕赵晚报记者安春华
石家庄曲艺类别的“非遗”项目并不算多,只有赵县两个项目列入省级保护名录(上期所说的木板书为藁城区“非遗”)。这仅有的两个省级项目,即赵县梅花调与赵县道情。目前梅花调的传承人还年轻,当地也有创作新作品的能力,而道情的传承人已经去世,目前还没找到能接替他的人。
图:赵县梅花调《骨肉情深》梁素霞演唱
图:赵县梅花调《骨肉情深》(梁素霞演唱,张金礼、曹丽敏伴奏)
图:赵县梅花调《骨肉情深》(梁素霞演唱,张金礼、曹丽敏伴奏)
我们自己的鼓曲
上周五,在赵县文化馆一间排练室里,我再次享受视听盛宴。传承人梁素霞(演唱)、馆长张金礼(三弦伴奏)、副研究馆员曹丽敏(扬琴伴奏),联手为我们献上了一段赵县梅花调《骨肉情深》。挺好听的,这是我最初乃至现在的感觉,但当时除了“好听”,一时竟找不到更多的词来形容。
《骨肉情深》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,是歌颂周总理的作品,由当时的音乐工作者梁奇、赵县文化馆老馆长王京辰等人集体创作。“这是经音乐工作者挖掘、整理、加工以后的作品,因为老艺人们都去世了,也没有留下声像资料,目前,这就是我们赵县梅花调最原始的东西了。”张金礼说。
由于在现场只听到一段,回来以后,又打开张馆长送我的“非遗”申报片光盘,并从网上搜各种鼓曲来听,试图加深印象,并横向比较,来感受曲种特点。但这次非常失败,我“泡”进各种鼓曲的“味儿”里,到最后也说不清谁和谁的区别,似乎有三弦伴奏的东西都是一种共同的“味儿”。最后,还是在鼓曲爱好者宋景山的帮助下,才理清思路:流行于京津地区的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(注意,梅花大鼓和赵县梅花调不是一个曲种),节奏明显舒缓很多,就像上期所说,以韵味醇厚、回味悠长而著称。从京津向南,冀中的西河大鼓、沧州的木板大鼓、冀南的梨花大鼓、山东的山东大鼓,它们的“雅劲儿”下去一些,而以内容加方言来接地气的“土劲儿”浓厚起来。此处“土”并非贬义,就像鲍鱼对于咱河北老乡,可能不如一碗炖肉吃着香。赵县梅花调,比之京韵大鼓、梅花大鼓、沧州木板大鼓等曲种,加快了节奏,虽然不离鼓曲的味道,尤其是开头几句,缓慢、深广、潇洒、抒情,一下子就能把人的耳朵“抓”住,但同时,民歌的感觉也挺浓(仅就《骨肉情深》等新作品来说),旋律优美流畅。《河北曲艺资料》一书收录了梁奇写的一篇《梅花调初探》,作为音乐工作者,他概括梅花调的特点:朴实而又流畅,丰富而又洗练,多变而又有规律,板式齐全成套,“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曲种。”
更重要的是,这个“比较完美的曲种”,是我们石家庄自己的鼓曲。“我们一直认为,梅花调是赵县独有哩,可是申报非遗的时候,省里评定时,认为是从山东传来的,有的专家这么说。我们本县人对这个说法并不满意。”张金礼说。
梅花调曲谱
梅花调伴奏乐器之书鼓、月牙板
梅花调伴奏乐器之书鼓、月牙板
图:梅花调伴奏乐器之大三弦
以赵州为中心
《石家庄市文化志·曲艺》中没有收录梅花调,是不是当时梅花调流行于石家庄东南部、较少在市区演出而被志书编写者们忽略了?情况不得而知。关于梅花调的起源,梁奇在文章中说:“文字上查无依据,只是在访问中艺人们都认为,最初是从山东流传过来的。他们的师父和师爷们讲,一百多年前的梅花调还被称为‘山东梅花柳儿’呢。后来,在多年的演唱过程中,群众才慢慢称其为‘梅花调’,俗称‘鼓碰弦儿’(因为以鼓和板领弦,而不像西河大鼓弦领鼓)。”
确实,宋景山也注意到,梅花调演唱者开始前总要先敲一下鼓帮,之后鼓、板、弦、琴齐奏,这敲鼓帮的动作,即为鼓领弦的信号。宋景山说,传统的梅花调只有鼓、板、弦,扬琴是后来加的。
梅花调“大约在明末清初就有了”,梁奇在文章中说,“清朝中后期盛行一方,这个时期在鲁西、冀南、豫北到处都有梅花调演唱活动。尤其是冀南,即现在的石家庄以南至邢台地区,约在八十到一百年以前更为风行。当时的梅花调和西河大鼓,依现在的石德线为界,各占南北。梅花调被称为‘南口’,西河大鼓被称为‘北口’,‘南口’到保定、沧州一带行不通,站不住;‘北口’到冀南也行不通站不住。”
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梅花调知名艺人,据梁奇调查,遍及南宫、辛集、宁晋、栾城、束鹿、藁城等地。其中,赵县艺人非常多,有吕增瑞、李占祥、张庆彬、王纪堂、吕振生、吕长友、吕狗皮、张全志、老鹰(艺名)、王同胜、王明记、范胖子、鲁晨兰、李瑞旭等。
今年55岁的梁素霞就是跟吕增瑞和鲁晨兰学的。70年代,她是文艺宣传队的一员,经常下乡演出。她向老艺人们学习,但没有按过去风俗磕头递帖,论字排辈。不久她就被县文化馆吸纳进来,成为文化馆在职人员。梁素霞说不清她的师父的师父是谁。据梁奇调查,吕增瑞的师父是栾城谢玉台,谢玉台的师父是南宫杨老孔,据说杨老孔的师爷可能是南宫县的说书状元张凤梧。
梁奇在他的文章里如数家珍一般罗列艺人名字,但这些名字于我们来说陌生又遥远,提不起探究的兴味。其实,调查传承谱系也就是了解曲种的发展历程,梁奇发现,一百多年前,梅花调起码在赵县、栾城、束鹿、藁城、宁晋、南宫一带是很兴盛的。“不过由于这个曲种难学难唱,又因地方局限性大(唱腔与这一带的土语紧密结合),致使其没有流传到更多更大区域,没有形成很多流派。所以,约在五十年前,因河南坠子、鼓子快(木板书)在这一带兴起,这个流行地区以赵州为中心的梅花调就渐渐衰落下来。”
图:赵县道情老艺人李顺堂(赵县文化馆供图)
视频2:赵县渔鼓道情小段《小两口抬水》李顺堂演唱
嘴上都有表情
赵县的另一种曲艺“大寺庄道情”,应该就是民间常说的渔鼓道情。大寺庄村老艺人李顺堂已经去世,没有徒弟。他生前留下一段录像,被剪辑编进非遗申报片中。那是一个小段《小两口抬水》,内容与木板书小段《抬水》基本一样。说实话,年愈八十的李老师傅,唱起来免不了豁牙漏风的,估计代表不了他此生的最高水平,能否代表石家庄曾经的最高水平也很难说。但这段极其珍贵的录像,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道情——它曾经风靡一时,如今踪影难寻。
“小时候俺姥娘一听见说道情的呀,就走不动道儿。”在姚栗村人司双印老先生家里,他兴致勃勃向我讲述道情艺人康长子(外号“大嘴”)的风采。“他身上斜挎一个长筒形的鼓,有一米来长,手指头一敲,声音和一般的鼓不一样,不是嘭嘭嘭、咚咚咚,而是腾腾腾,旁边他那个搭档,手拿一片钹,敲出来声音是灿灿灿。腾腾腾、灿灿灿,俺姥娘一学,俺就知道这是说道情的来了。”
司双印经常跟着姥娘听道情,对康长子印象深刻。“这个大嘴,不但身上有戏、脸上有戏,连嘴上也有戏,一看他那个表情呀,人们就不想走,自愿给他钱。一般的说书人,比划武打,捎带简单的口技,这是一般人。大嘴不一般在哪儿?除了身上、脸上,他嘴上都有动作,撇嘴、咧嘴、抿嘴……特别迷人。人们给他起外号大嘴,可不光是因为他嘴大!”
当时,还是孩子的司双印每每跟着姥娘到市区西花园听书,听过大半天,小孩子不耐烦了,一个劲儿拽姥娘衣服:走吧,走吧,可是拉不动。直到天黑散场,小脚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孩,颠儿颠儿走回孙村。
康长子,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市区西花园的渔鼓道情艺人之一。据《石家庄市文化志·曲艺》记载,当时除他之外,常在西花园演出的还有罗成富、罗淑梅、刘吉祥、李合新、申成和、孙春义、白志兰等多位艺人。而康长子口述、连承裕整理的《我的艺人生涯》,回忆在年至年,聚集在西花园的渔鼓道情艺人“最高峰时多达70余人”。
图:赵县道情老艺人李顺堂与搭档合说道情(赵县文化馆供图)
图:赵县道情老艺人李顺堂(赵县文化馆供图)
图:赵县道情老艺人李顺堂(赵县文化馆供图)
“孙赵门”与“杨门”
康长子是本市北翟营村人,师从罗成富。他的口述文章中没有追溯传承谱系,不知他入的是哪一门。赵县大寺庄村李顺堂,小时候在大安剧场看戏,中午休息时自发说书一段,观众喝彩不停,显现出艺术天赋。后来,拜隆尧县韩志忠老先生为师学艺。而韩志忠师从于谁,属于哪一门,现在也查不出来了。
上期我们写到的木板书艺人马瑞平,属于“孙赵门”,她的师爷申成合是既会说道情也会说木板书的全能人才。百度百科“河北渔鼓道情”词条,是这一曲种最详细的资料,我在网上搜不出它的出处,但请精通曲艺的宋景山先生看过,认为除了个别细节,绝大部分内容与他了解的情况都相符。据此词条,道情在石家庄市及元氏、赞皇、高邑、赵县、栾城、宁晋、藁城、柏乡一带曾一度盛行。清朝以来,河北的渔鼓艺人分属“孙赵门”和“杨门”两大派系。“据元氏县和赵县的老艺人回忆,清康熙年间,南方一道士来冀南收徒传授渔鼓,言称属孙赵门,并排定了其传人的辈序占字为:禄、尧、启、进、新、春、善、青、陈、伦、天、增、喜、成、先。从此,孙赵门这一支派便在冀南、冀西传播流行。知名艺人有杨新尚、李新恭、周春风、张春太、殷善坤、殷善其等。其中‘春’字辈和‘善’字辈艺人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,此间是河北渔鼓的鼎盛期。”
该词条说,“杨门”渔鼓传入河北时间不详,活动范围在冀南,传人辈序占字分别是:道、德、同、玄、静、振、长、守、太、清、一、杨、来、付、本、合、教、永、元、明、智、礼、忠、诚、信、希、维、彦、子、宁、士、景、荣、玉、茂、崇、高、思、发、兴、大、庙、东、皇、会、朝、圣、乐、辉、登。已知的杨门名艺人有蔡富海(明字辈)、杨智兴(小名“蛤蟆”)、白智兰、张智宾等。“孙赵门”和“杨门”两个支派在书目和演唱方法上没有明显的区别。
研究杨门的辈序占字,很有意思,首先,“道德”、“玄静”、“太清”等字眼,透露出渔鼓道情与道教的关系。相关资料说法也都一致:渔鼓道情可追溯至唐宋,最初是道士们传道或者化募时说唱的曲目。到了元代,渔鼓已广为传唱,《元史》(卷一百五)中说:“诸民间子弟,不务生业,辄于城市坊镇,演唱词语,教习杂戏……击渔鼓,惑人集众。”明清时期,渔鼓已形成了“有板有眼”的完整唱腔。明清思想家王夫之曾作过《愚古词》(愚古即渔鼓)二十七首。作者说:“晓风残月,一板一槌,亦自使逍遥自在。”(《船山遗书》第六十四册)由此,渔鼓道情由宣扬道教思想的工具,演变为民间说唱艺术。
渔鼓道情大约在明末清初传入河北。明嘉靖年间刊印的《霸州志》,谓元末霸州名倡李哥“所歌皆仙曲道情”;清代李声振所作《百戏竹枝词》,有《唱道情》一诗云:“拍板曾传蓝采和,黄冠一曲缓相过。听来鲨鼓歌云笈,真是鱼山唱贝多。”诗序说渔鼓乃“道士曲,以鲨鱼皮鼓、竹板节歌”。这些资料表明,明清两代河北即有渔鼓道情流行。
图:(这张最好用上,专门去拍的)上世纪80年代,司双印在南长街一集贸市场上偶遇康长子,与之合影。康长子时年78岁,在市场上卖席子。(安春华翻拍)
图:道情所用乐器:渔鼓、简板、钹(赵县文化馆供图)
图:古老的道情书目(赵县文化馆供图)
有这么多字,有这么多人吗?
研究“杨门”辈序占字的另一个发现是,赵县人杨智兴如果占“智”字辈,那么,尽管此门派的创立者希望这个曲种长久地传下去,早早排定一大堆字,但现实情况却是,还有很多字没用上呢,就没有人了。不是吗?据老家宁晋县的宋景山说,杨智兴小名蛤蟆,赵县沙河店镇西杨村人,因与宁晋县毗邻,宁晋许多人都知道他。他大约是-年代生人。
曲艺这种艺术也是有它自然的兴衰起落,这种起伏周期,比戏曲好像要短。人们一个曲种听了二三十年,当听到新味道新感觉时,自然会转移视角。比如上世纪40年代流行木板书,后来河南坠子传入,木板书被冲击得厉害。那么更古老的渔鼓道情,就不用说了。《石家庄市文化志》记载:“渔鼓道情唱腔苍劲有力、淳朴憨厚。乍听类似单词,平心静听,自有妙处。”这苍劲有力、淳朴憨厚,从李顺堂老人的录像中,我感受到了。它一出场即冒着浓厚的“土味儿”,上来先说几句白话:“说墙上画狗不咬人,蒜臼子活面不能当盆,要哩当不了亲生子,闺女大了是人家哩人!”几句大实话,瞬间拉近与观众的距离。
尽管如此,能够像专家那样“平心静听”,进一步体会其“自有妙处”的人,越来越少,或者可以说,几乎没了。当年随着道士们的传道,渔鼓流布全国,仅粗略查找,即有金华道情、陕北道情、四川竹琴、安徽萧县渔鼓道情、湖南渔鼓、桂林渔鼓,列为国家级“非遗”,另外还知道河南周口市商水县的渔鼓道情(省级非遗)也很有名。但是,都是仅有个别人会,传承堪忧。
“不是这些东西不好听,而是现在的人听不惯了。”张金礼说,赵县有“三鼓一调”:扇鼓、战鼓、背灯挎鼓、梅花调,“县里早就这么提,可是看这架势儿,是光想把这一调给‘揶’了。”揶,当地土话,你懂的。“我们打算先找一批40来岁、有戏曲基础、过去跟文化馆学过的人,成立队伍,参加比赛、演出,争取走出国门。将来再找一批年轻人学。”张金礼本人会作曲,他有创作梅花调新书目的能力,梅花调还能向前发展。比较来说,道情的传承更困难些。文化馆准备首先收集老艺人的遗物——鼓板、剧本、衣服等,然后再找一找会说一点儿的人,录音录像,如果能积攒起一些录音录像,将来在此基础上挖掘整理,或许能创作新的道情作品。
写到最后,我想提一部电影:《有话好好说》(姜文、李保田主演)。记得电影中很奇怪但是又很和谐地插入了一段曲艺说唱,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,现在查查,是北京琴书。因为这部电影,好多人第一次领略了琴书那难以言说的“味儿”。我们石家庄既然有自己的鼓曲,梅花调、木板书,能否就用它们来创作一两首说唱石家庄、说唱石家庄人的小段?听马增慧唱的单弦《北京人儿》是多么的好啊,如果能有这样的小段走红网络,不但对石家庄是一种宣传,而且这两个曲种也就有传播推广的希望了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